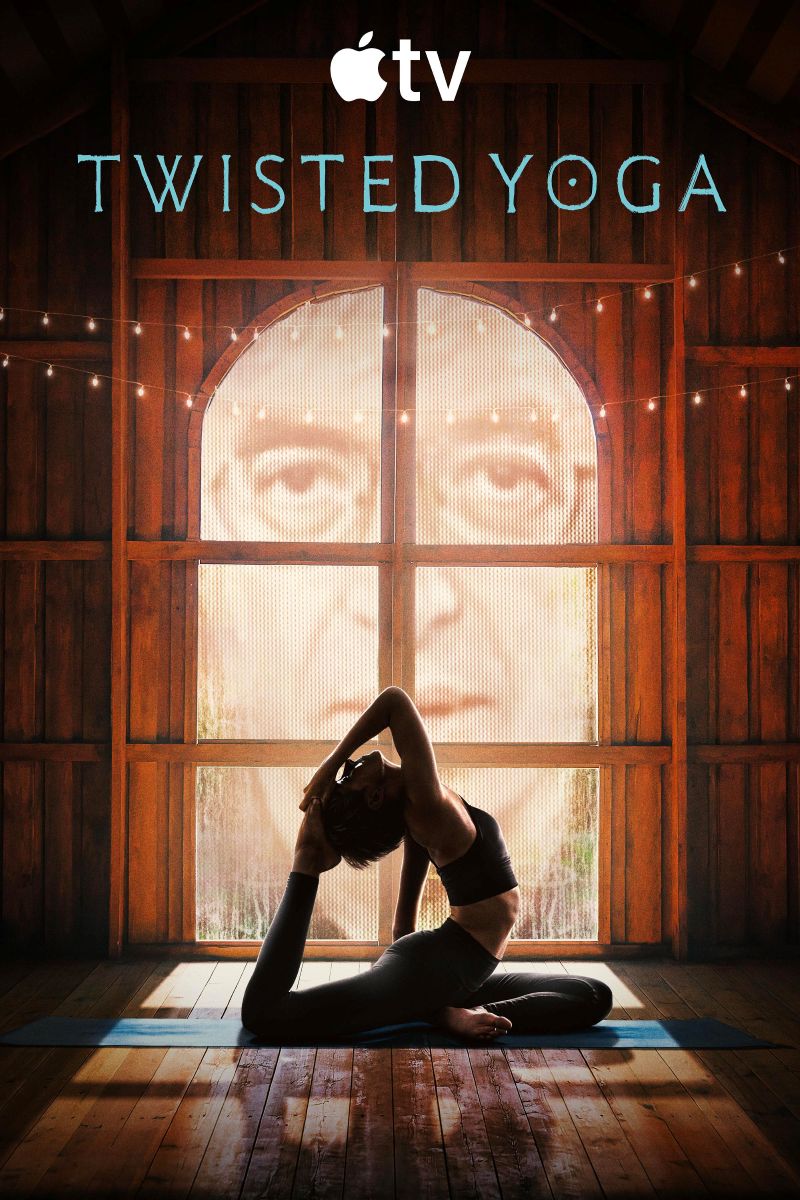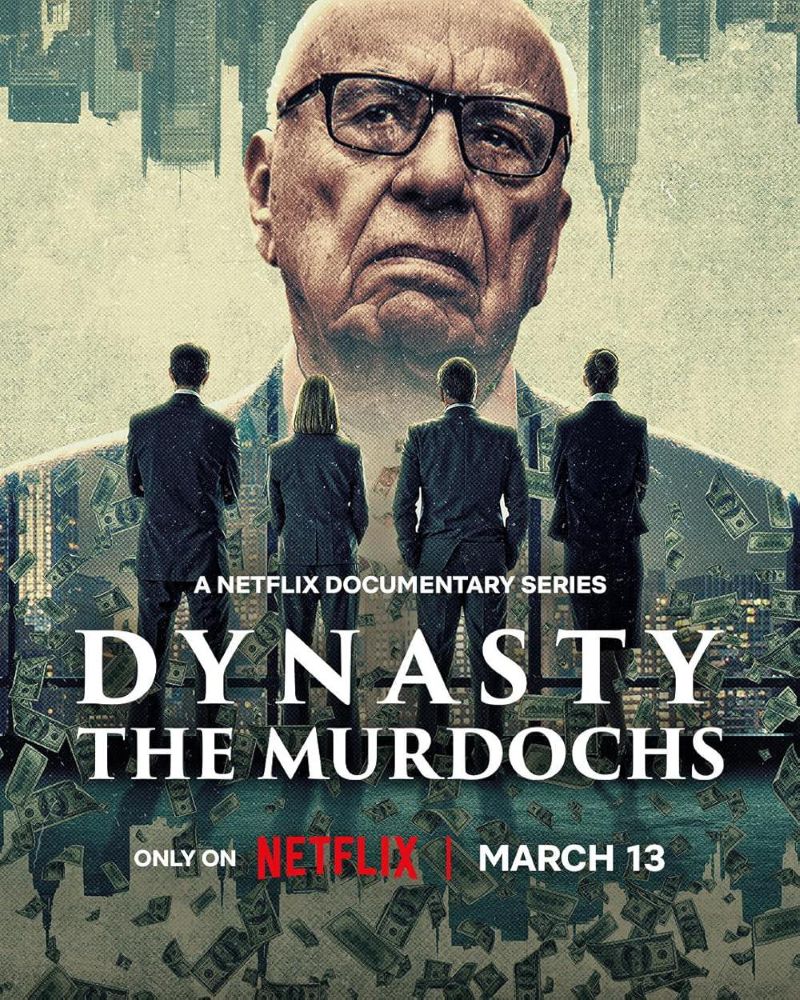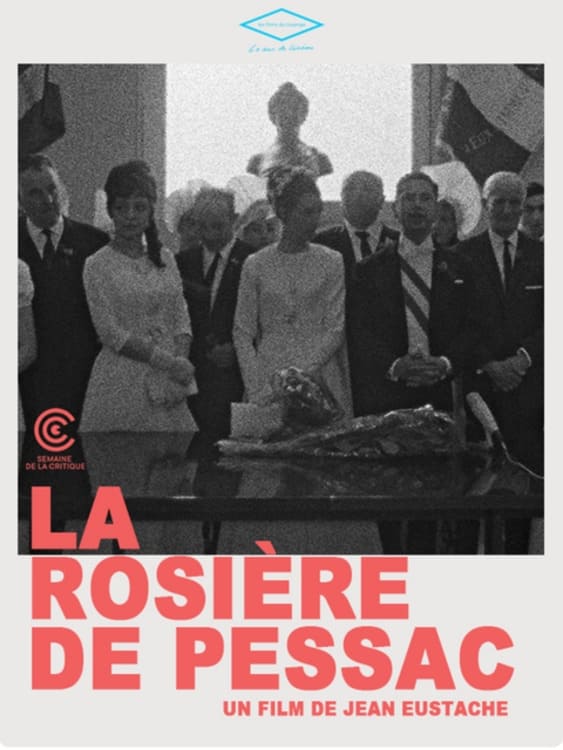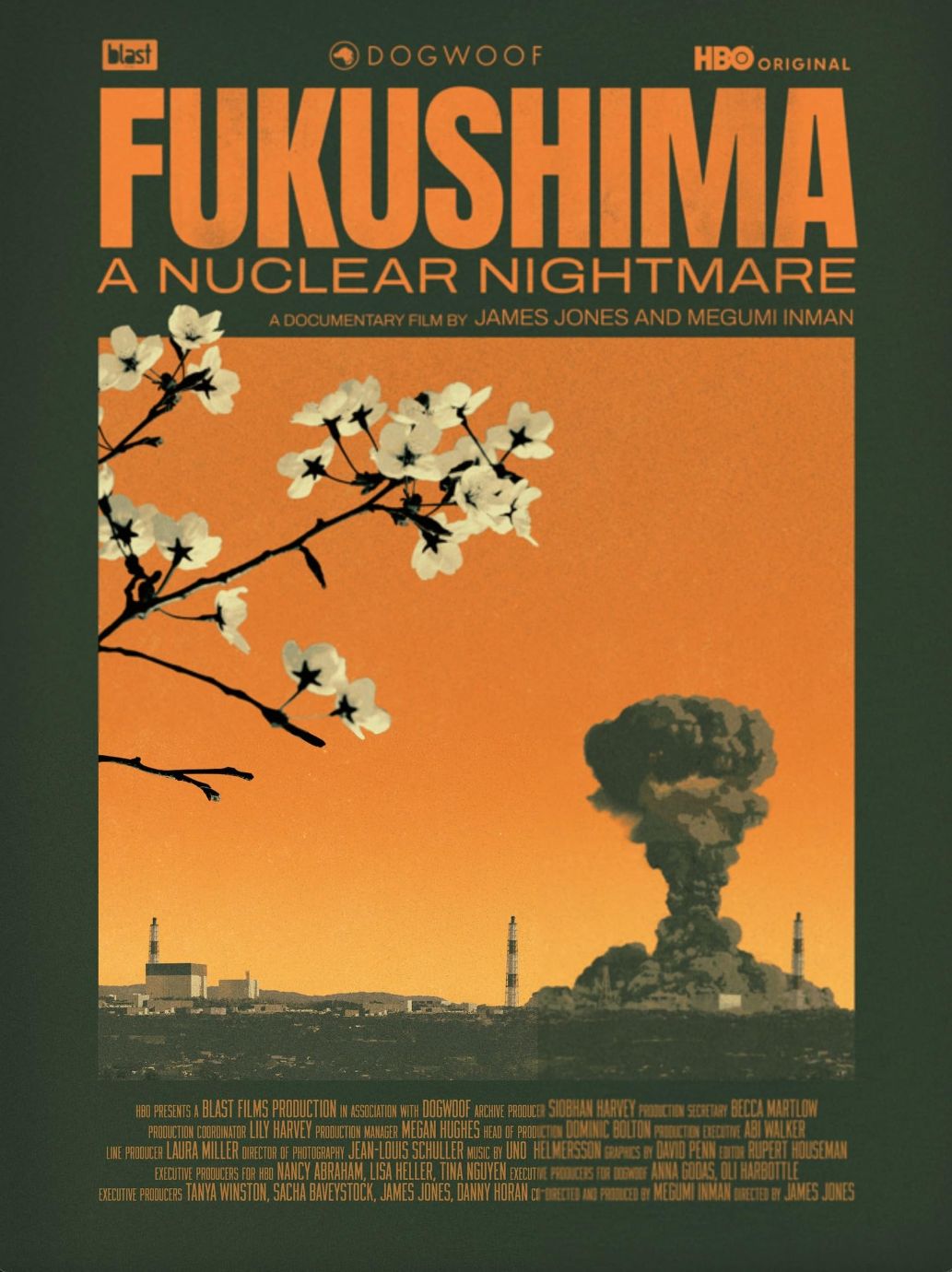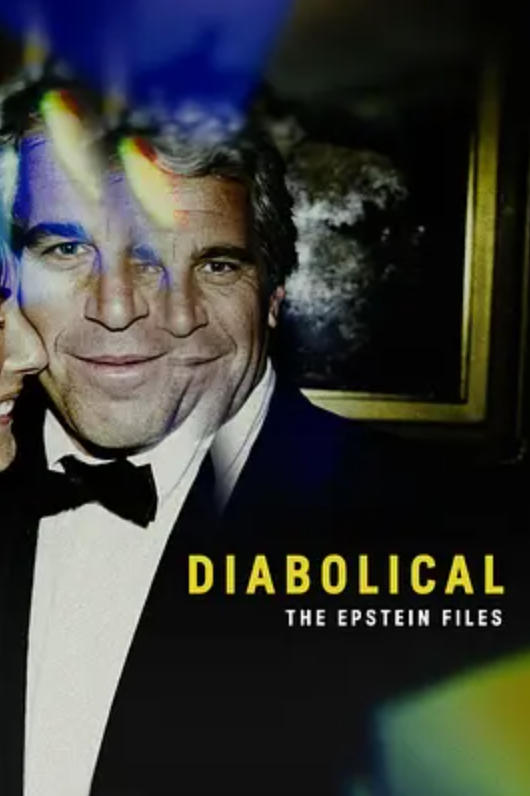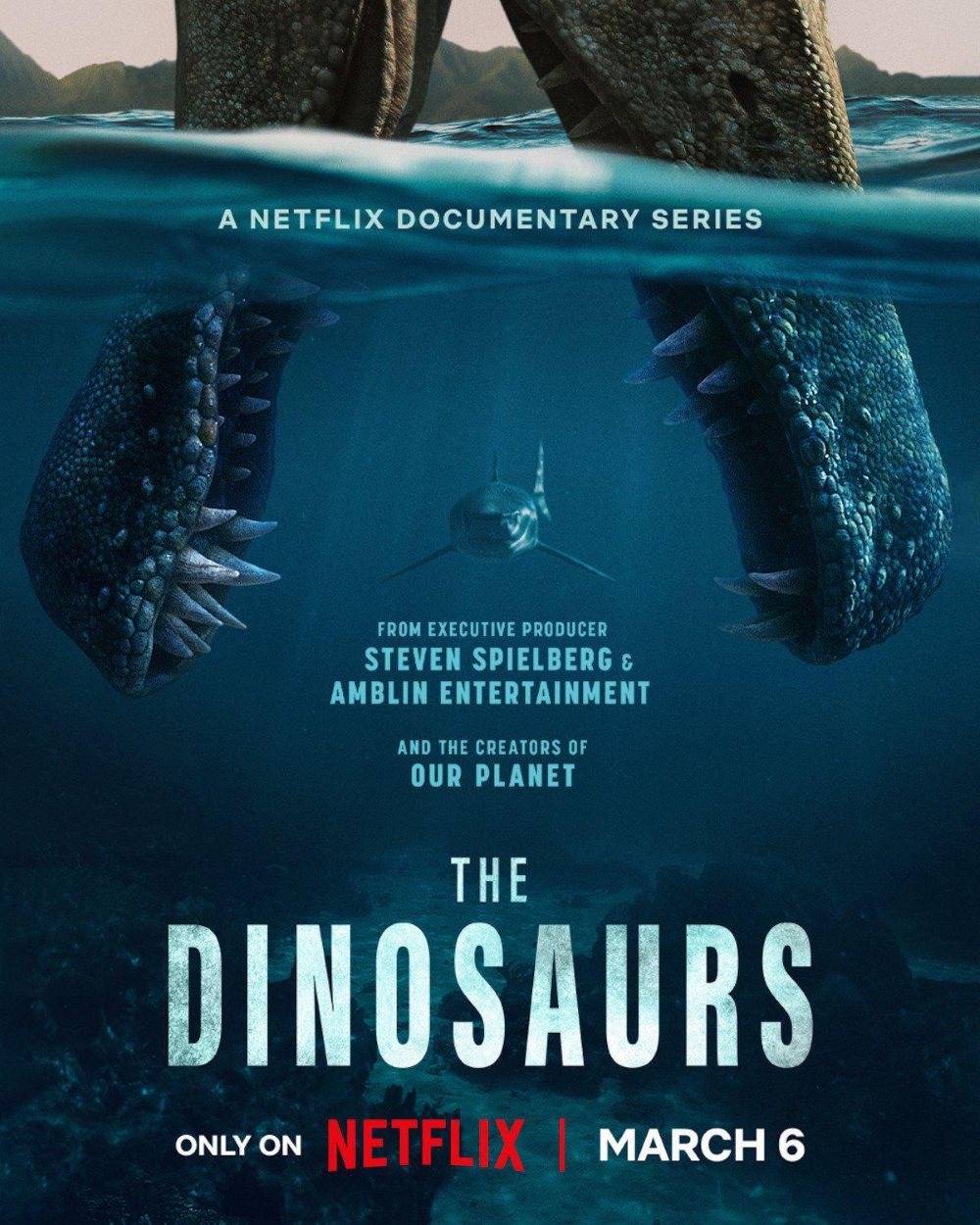|
°įő“ő™ ≤√īňĶ£¨ľÕ¬ľ∆¨Ķľ—›Ķń…Ū∑› «ĪįőĘĶń£Ņń„÷Ľń‹÷“ Ķ°Ęĺ°Ņ…ń‹÷“ ĶĶōĹę…ķĽÓ◊™ĽĮő™”įŌŮ£¨»őļő唳ŖŃŔŌ¬Ķń…ů ”ļÕőš∂Ō£¨∂ľĽŠ Ļń„Ķń”įŌŮŅ…“…°£ń„√Ľ”–»®ņŻ»•—ňłÓňŁ°£°Ī

≤…∑√’Ŗ£ļőńļ£ ‹∑√’Ŗ£ļŃ÷Ųő Ō÷ Ķ…ķĽÓ÷–Ķń…ý“Ű£¨◊„“‘÷ß≥÷∆ū”įŌŮĶńŅ’ľš őńļ££ļń„◊ÓŌ≤Ľ∂ň≠Ķń◊ų∆∑? Ń÷Ųő£ļő“ł’Ņ™ ľ√‘ŃĶňĢŅ…∑ÚňĻĽý,ļůņī «∆ś ŅņÕňĻĽý°£⽼ňĢ «“Ľ÷÷Ļů◊Ś∆Ý£¨∂Ū¬řňĻňľŌŽĶńĻů◊Ś£¨∑«≥£Ķń“’ ű£¨°∂ĶŮŅŐ ĪĻ‚°∑ «ő“Ķń’ŪĪŖ ť£¨ŅīŃňļ‹∂ŗĪť°£ļůņīĺűĶ√’‚÷÷Ļů◊Ś∆ÝņŽő“√«ĶĪŌ¬Ķń…ķĽÓļ‹ ‘∂£¨ĺÕ «≤ĽĹ”Ķō∆Ýį…£¨ňŻĶń–ő∂Ý…Ō—ßļÕő“√«ĺŗņŽļ‹‘∂°£ļůņī√‘ŃĶ∆ś ŅņÕňĻĽý£¨“ÚňŻņŽő“√«ļ‹ĹŁ£¨ń«÷÷īīÕīő“√«ń‹ł–ĺűĶĹ°£Ī»»Á°∂ ģĹŽ°∑÷–Ķńń«÷÷ŃĹń—£¨‘ŕ…ķĽÓ÷–ő“√«ļÕňŁ”–Ļ≤√ý°£Ķę «ő““ņ»ĽĺűĶ√ňŻļ‹“’ ű°£ ļůņīĺÕ «√‘ŃĶ∑®ňĻĪŲĶ¬ļÕļ…ňų£¨ŐōĪū «∑®ňĻĪŲĶ¬Ķń◊ų∆∑£¨ľ‚»Ů£¨ń«÷÷ņšņšĶńŌ∑ĺÁĻ‚£¨”––©“≤ļ‹ī÷≤ŕ£¨Ķę «ňŻĶń…ķ√ŁļÕ◊ų∆∑ «ÕÍ»ęļŌ⼀£¨ő“ń‹ł–ĺűĶĹń«÷÷ѶŃŅ°£ňŻ”––© «łńĪŗ◊‘Īū⼈Ķń◊ų∆∑£¨Ī»»Á°∂įōŃ÷—«ņķ…ĹīůĻ„≥°°∑łńĪŗ◊‘Ķ¬≤ľŃ÷ĶńÕ¨√Ż–°ňĶ£¨ĶęŅīÕÍļů£¨ń«÷÷∆Ý÷ £¨∑®ňĻĪŲĶ¬Ķń∆ÝŌĘļÕňŻĶń”į⽚ÕÍ»ęÕ¨“Ľ°£ń„Ņ…“‘≤ĽĻżňŻń«÷÷…ķĽÓ£¨“≤Ņ…“‘≤ĽŌ≤Ľ∂ń«÷÷…ķĽÓ£¨ĶęňŻĶń”į∆¨ļÕňŻĪĺ»ň «ÕÍ»ęļŌ“ĽĶń°£ »Ľļů‘ŔŅīļ‹ĻŇĶšĶń∂ęőų£¨į≤’‹¬ř∆’¬ŚňĻ£¨ő““≤∑«≥£Ō≤Ľ∂£¨ĶęŌ÷‘ŕĺűĶ√Ѷ∂»≤ĽĻĽ£¨ĺűĶ√≤ĽĻżŮę°£ľÕ¬ľ∆¨ő“ŅīĶ√ÕŪ£¨ļ…ňųĶń°∂Ľ“–‹»ň°∑ «ńŅ«į ő“ŅīĶĹĶńľÕ¬ľ⽚÷–’ūļ≥◊ÓīůĶń”į∆¨°£ŅīÕÍń«≤Ņ”į∆¨ļů,ő“ĺűĶ√ ≤√īľľ ű∂ľ≤Ľ÷ō“™Ńň£¨”–łŁ÷ō“™Ķń£¨≥¨‘Ĺľľ ű≤„⾯√ś∂ÝĪō–ŽŅľŃŅĶń ¬«ť°£ňŁÕÍ»ę «“Ľ≤Ņ≤ĽĽŠŇńĶÁ”įĶń»ňŇńĶń£¨ĽķőĽ‘ŕń«∂ýļķ’ŘŐŕ£¨ĶĪ»ĽľŰľ≠ «ļ…ňų£¨ňŻ≤ĻŇńŃň–©ĺĶÕ∑£¨◊ÓĪĮ≤“Ķń «ń«»ň”Ųļ¶Ķń…ý“Ű£¨ňŻĺÕŇń◊‘ľļ‘ŕń«∂ýŐż£¨ňŻ√Ľ”–ňĶĽį°£»Ľļů£¨ĶĪňŻŇńń«»ňĶń«įŇģ”—”Ųļ¶Ķń…ý“Ű Ī£¨÷Ľ «ňĶ£ļ°łŐęÕīŅŗŃň£¨Ō£ÕŻń„≤Ľ“™Ī£īś£¨į—ňŁ…ĺĶŰį…°£°Ļ’‚—ý’‚Ō∑ĺÁĶń∑›ŃŅĺÕ“—ĺ≠ĶĹőĽŃň°£ń«≤Ņ”į∆¨∂‘ő“Ķń”įŌž∑«≥£⼤īů°£ ∆šňŻ»ňĶń“Ľ–©”į∆¨»ī÷Ľ”√‘ŕľľ ű»•°łŅŔ°Ļ£¨ő“ĺűĶ√ĺÕ√Ľ”–“‚ňľŃň°£ňý“‘£¨ő“”– ĪŅľ¬«£¨“≤‘ŕ’ű‘ķ°£ń„ŌŽ‘ŕľľ ű…Ō£¨łų∑Ĺ√ś∂ľ◊ŲĶ√ļ√£¨Ķę‘ŕ√Ľ”–įž∑®ŃĹ’ŖľśĻňĶń ĪļÚ£¨ľľ ű «∑Ů“™◊ŲĶ√ļ‹Ļ‚(÷ł–ř őŐęĻż£¨ ß»•‘≠Īĺ÷ ∆”÷ģ∂Į»ňѶŃŅ)£Ņ’‚ «ő““Ľ÷ĪňľŅľĶńő Ő‚°£ Ķľ …Ō£¨ľÕ¬ľ∆¨ĶńѶŃŅ£¨łŁ÷ō“™Ķń «Ĺť»Ž…ķĽÓĶń…Ó∂»°£ňŁ «’ŻŐŚĶń≥ Ō÷£¨∂Ý≤ĽĹŲ «Ľ≠√śő Ő‚°£Ľ≠√śĶĪ»Ľ“≤ «“ĽłŲŅľŃŅ£¨Ķę’‚łŲĽ≠√śĽýĪĺ…ŌļÕń„Ňń…„ĶńŐ‚≤ń°ĘļÕń„Ķń»ň «“Ľ÷¬Ķń°£ňŁ≤Ľ «Õ‚‘ŕĶń£¨ľŔ»ÁňŁ «Őý∆¨£¨Őý…Ō»•ĶńĺÕĽŠ∑«≥£≤Ľ ś∑Ģ°£ őńļ££ļ‘ŕ“Űņ÷∑Ĺ√śń„”–ļ‹…ÓĶń–ř—Ý£¨Ķęń„Ķń”į∆¨÷–ļ√ŌŮī”ņī≤Ľ”√“Űņ÷°£ Ń÷Ųő£ļ∂‘°£Īū»ňĺÕő —Ĺ£°“Úő™ő“”Ķ”–ŃĹ°Ę»ż«ß’Ň“Űņ÷≥™∆¨£¨ī”łŮņÔłŖņŻ •”Ĺ(Gregorian chant)ĶĹ∂Ģ ģ ņľÕĶń‹ųį◊Ņň(Arnold Schönberg)°Ę ∑Őōņ≠„ŽňĻĽý(Igor Fyodorovich Stravinsky)Ķ»ő“»ę”–°£”–“Ľ∂ő Ī∆ŕő“∂‘“Űņ÷Ō¬ĶńĻ¶∑ÚĪ»√ņ űĽĻ“™∂ŗ°£”–Ňů”—ő ő“, ő™ļő≤Ľ”√“Űņ÷—Ĺ?ő“∑ĘŌ÷£¨”––©”į∆¨£¨Ń¶ŃŅ≤ĽĻĽĺÕ”√“Űņ÷»•š÷»ĺ∆Ý∑’£¨’‚ «≤Ľ∂‘Ķń°£ő“ĺűĶ√…ý“Ű©§©§Ō÷ Ķ…ķĽÓ÷–Ķń…ý“Ű£¨◊„“‘÷ß≥÷∆ū”įŌŮĶńŅ’ľš°£ňý“‘£¨ő“ĺ°ŃŅ”√ňŁĪĺ…ŪĶń…ý“Ű»•◊Ų£¨≤Ľ»•Őý“Űņ÷°£ ĶĪ»Ľ“≤”–»ň”√Ķ√ļ‹ļ√£¨Ī»»Á∆ś ŅņÕňĻĽý°£ő“‘ŕ°∂≥¬¬Į°∑’‚≤Ņ∆¨◊”ņÔ”√ŃňĶĪĶōĶń“Űņ÷, ļÕń«łŲŅ’ľš «ő«ļŌĶń°£»ÁĻŻ◊®√Ň◊Ų“Ľ∂ő“Űņ÷∑Ň‘ŕń«∂ý£¨ő“»Ōő™≤Ľ∂‘£¨÷Ľń‹”√ń«łŲŌ÷ ĶŅ’ľšņÔĶń…ý“Ű°£’‚ «ő“Ķńľ∆ĹŌ°£įŁņ®≤…∑√£¨ő““Ľį„≤ĽĽŠŐōĪūį≤ŇŇ°£ňŻ◊Ý‘ŕń«∂ý£¨ĺÕ◊Ý‘ŕń«∂ý£¨ő“÷Ľ «’“ĽķőĽ£¨į—Ľķ∆ų“Ľľ‹‘ŕń«∂ýĺÕÕÍŃň°£ő“≤ĽĽŠňĶń„◊Ýń«∂ý°Ęń«∂ýļ√÷ģņŗĶń°£ő““Ľį„≤ĽĽŠń«—ý»•»į£¨ňŻŌįĻŖ‘ŕń«∂ý◊Ý£¨ŅŌ∂® «ňŻ ļŌĶńĶō∑Ĺ£¨ňŻĶń“ő◊”∑Ň‘ŕń«ņÔ£¨Õýń«∂ý“Ľ◊Ý£¨÷‹őßĶńĽ∑ĺ≥£¨Ķ∆Ļ‚£¨∆Ý∑’ÕÍ»ęļŌŇń£¨ĺÝ»Ľ «∂‘Ķń°£ Ō„łŘ∑ÔĽňĶÁ ”Ő®ĶĹ…¬őų»żņÔ∂ī◊Ų◊®Ő‚ĹŕńŅ£¨“≤ «ő“Ńž◊Ň»•Ķń£¨ňŻ√«Ňń Ī£¨ĽĻīÚĻ‚£¨“ĽŌ¬◊”ŅůĻ§ĶńŃ≥…ęĺÕĹ°ŅĶ∂ŗŃň£¨ļ‹Ī•¬ķ°£ń«÷÷≤ŗĻ‚ĽĻīÝ–©∑īĻ‚£¨ĪÍ◊ľĶńĻĻÕľ°£ļůņīő“ŅīŃň∆¨◊”£¨ĺűĶ√ń«÷÷∆Ý÷ ≤ĽŌŮňŻ√«£¨ł–ĺűÕÍ»ęĪšŃň£¨ňŻĪšĶ√≤Ľ «ń«łŲ»ňŃň°£ń«÷÷įĶįĶĶń”įĶų£¨ňŻ√«ľ“ĺÕ «ń«—ý£¨√Ľ”–ń«√ī⼤īůĶńĻ‚‘ī£¨įĶįĶĶń£¨ľ“ĺŖņŌņŌĶń£¨ļ‹∆∆ņ√£¨ĺÕ «ń«÷÷∑’őßļÕ≤‘ņŌĶń»›—’£¨ń«÷÷ł–ĺű”ŽňŻ «Õͻꓼ÷¬Ķń£¨įŁņ®…ý“Ű°ĘŅ’ľš°£÷‹őß“≤–Ū”– ’⾳“ŰĽķĶńņģį»…ý°ĘĶÁ ”Ľķ…ý°ĘÕ‚√ś◊ŖņīĶńĹ–¬Ű…ý£¨’‚–©∂ľ «ňŻ…ķĽÓ÷–Ķń“Ľ≤Ņ∑÷£¨ő“ĺűĶ√ī”Ļ„“Ś…ŌĹ≤£¨’‚»ę «“Űņ÷°£ °∂»żņÔ∂ī°∑◊ÓļůĶńń«∂őŇšņ÷£¨ «ő“Ķŕ∂Ģīő»•ő““Őłłľ“£¨ňŻ√«’ż‘ŕ≥™ •łŤ£¨ń« «ő“īĢ◊ŇĶń°£ŇńňŻĶń ĪļÚ£¨‘≠Ō»‘ŕ’“ņŌ’’∆¨£¨Ňń◊ŇŇń◊Ň£¨ŐżĶĹ“ĽłŲ…ý“ŰŐōĪūļ√Őż£¨“‘ő™ « ’“ŰĽķ°£ļůņīĺűĶ√≤Ľ∂‘, ∑ĘŌ÷ļ√ŌŮ «”–»ň‘ŕŌ÷≥°≥™£¨≤Ľ « ’“ŰĽķ≤•∑ŇĶń°£ő“ “ĽŇ§Õ∑£¨ŅīľŻ ő““ŐļÕŃŪÕ‚“ĽłŲ–ŇÕĹŇŅ‘ŕń«∂ýĶĽłś£¨ő“ŃʬŪĹę…„”įĽķŇ°ĻżņīĺÕŅ™ ľŇń£¨ń«łŲ ĪļÚĺűĶ√’‚łŲ“Űņ÷ŐōĪūļ√°£ļůņī£¨ő“ňĶ:°łń„ĽĻĽŠ≥™¬ū?°ĻňżĺÕ≥™łÝő“Őż°£ő“ĶĪ Ī’ĺ‘ŕń«ņÔ£¨Őż◊Ň—ŘņŠĺÕŃųŌ¬ņīŃň, ő“į—Ń≥ҧŌÚÕ‚√ś°£ń« Īńļ…ę≤‘√££¨ő“ÕĽ»ĽĺűĶ√…ķ√Ł÷–ī”ņī√Ľ”–ŐżĻż’‚√īļ√Ķń“Űņ÷£¨ŐōĪū√ņ£¨≤¶‘ŕń„Ķń–ńŌ“…Ō£¨ «”Ô—‘őř∑®–ő»›Ķńń«÷÷ł–ī•°£ń«÷÷…ý“Ű∑Ň‘ŕ◊ÓļůŇńő“łł«◊Ķńń«“Ľ∂ő «ļŌ Ķń£¨łŤī ◊Óļů“Ľĺš°Ę◊ÓļůŃĹłŲ◊÷ĺÕ «°ł”ņ…ķ°Ļ, ’ż «ő“łł«◊Ķń√Ż◊÷£¨“≤ «”į∆¨◊ÓļůĶńŃĹłŲ◊÷°£ňý“‘£¨’‚ «ő“Ķń–ń∑Ň‘ŕń«∂ý£¨ő“į—ňŁ∑Ň‘ŕń«∂ý£¨ «ļŌ Ķń£¨ «◊ľ»∑Ķń°£ő“ĺűĶ√’‚∂ő“Űņ÷≤ĽÕĽō££¨ń„»ÁĻŻ‘Ŕ◊ų “ĽłŲ«ķ◊”∑Ň‘ŕń«∂ýĺÕ≤Ľ∂‘°£ ő“’‚ĽōŇń…„Ķń°∂īęĶņ»ň°∑£¨ő““≤‘ŕŅľ¬«»Áļőī¶ņŪ…ý“Ű°£ń«–©‘Ž“Ű“™≤Ľ“™≥ťĶŰ£ŅĪ»»Á£¨ő“‘ŕŇńń≥“ĽłŲīęĶņ»ňĶń ĪļÚ£¨Õ‚√ś“Ľ÷Ī”–∆Ż≥Ķ°ĘÕŌņ≠Ľķĺ≠Ļż£¨ő“ĺűĶ√ń«łŲ‘Ž“Ű≤Ľ”¶ł√»•ĶŰ£¨“Úő™ļůņīňŻĹ≤ĶĹňŻ√«Ķń∑◊’ý£¨ń«÷÷ÕīŅŗ°Ę’ű‘ķ£¨ń«÷÷‘Í∂Į°Ę∑◊¬“£¨ń« «…ķĽÓĶń‘Ž“Ű, “≤ «Ō÷ Ķ…ķĽÓ÷–īś‘ŕĶń…ý“Ű£¨Õ¨ Ī“≤Ņ…ń‹ «–ńŃť’ű‘ķĶńÕ‚ĽĮ£¨∑Ň‘ŕń«∂ýĶĪ÷ųĻŘ…ý“Ű”√“≤ «ļŌ Ķń°£ňŻĶń∑Ņľš’żļ√∂‘◊ҬŪ¬∑£¨ő“ĽĽ“ĽłŲ∑ŅľšĺÕ√Ľ”–ő Ő‚Ńň£¨Ķęő“≤Ľ‘ł“‚ő™Ńňį≤ĺ≤ĶńĽ∑ĺ≥»•ĽĽ∑Ņľš°£

ļ√ņ≥őŽń«÷÷√ų–Ň∆¨—ýĶń∂ęőųő“ ‹≤ĽŃň őńļ££ļŇń…„°∂»żņÔ∂ī°∑ «‘ű—ý‘Ķ∆ūĶń? Ń÷Ųő£ļ‘ŕ…Ĺ…ŌŇń°∂≥¬¬Į°∑ Ī£¨ő“√«Ľ≠ĶńĹ≤ĺŅő®√ņ£¨»ňľ“ňĶń„ń« «Ľ≠ľ“ŇńĶń£¨»ę «Ľ≠£¨“Ľ’Ň“Ľ’ŇĶń°£√ŅłŲĽķőĽ «įŕļ√Ķń£¨ĻŐ∂®°Ęň„ľ∆ļ√Ķń, ’ŻłŲ’¬ĹŕĶńĻĻ≥… «ŌŽļ√Ķń£¨–ő∂Ý…ŌĶń°£»ĽļůŇń◊ŇŇń◊Ň£¨ő“ÕĽ»ĽĺűĶ√ő“’‚ «¬√”ő’ŖĶń—ŘĻ‚°£ňš»ĽňŁ «…¬őųÕ≠ī®Ķń“ĽłŲ’Ú£¨Ķęő“»‘»Ľ «“‘Õ‚ņī»ňĶń—ŘĻ‚‘ŕŅī’‚łŲ’Ú£¨ňš»ĽŇńĶ√ļ‹√ņ°Ęļ‹√ņ°£ő“÷ĪĶĹŌ÷‘໑ļ‹Ő÷—Šļ√ņ≥őŽĶńĽ≠√ś£¨ń«÷÷√ų–Ň∆¨—ýĶń∂ęőųő“ ‹≤ĽŃň°£ »ňľ“ňĶő“Ō÷‘ŕŇńĶ√ļ‹ī÷≤ŕ£¨∆š Ķ’‚ «ő“ĺűőÚĻżņīĶń°£ĺÕ‘ŕ…Ĺ…ŌŇń…„°∂≥¬¬Į°∑Ķń ĪļÚ£¨ÕĽ»Ľ“ĽłŲĽ≠√ś‘ŕő“ń‘ļ£÷–£¨“Ľ≤ŅĶÁ”į‘ŕő“ń‘ļ£÷–ÕÍ≥…Ńň°£“Ľ≤Ņļŕį◊”į∆¨,‘ŕ’‚≤Ņļŕį◊”į∆¨÷–”–“ĽłŲ≤ …ęĺĶÕ∑£¨ «ņ∂Őž£¨ĪŐņ∂ĶńŐžŅ’£¨≤Ś‘ŕ“Ľ≤Ņļŕį◊∆¨ņÔ£¨‘ŕļŕįĶ∆¨◊”Ķń÷–ľš£¨”–“ĽłŲīŅĺĽĶńņ∂…ęĺĶÕ∑£¨ĶęňŁ≤Ľ Ű”ŕŅůĻ§,£¨ňŁ “Ľ÷Ī‘ŕő“Ķńń‘ļ£ņÔĽő°£Ňńő“ĶńłłĪ≤£¨ő“ĺűĶ√ń«łŲŅ…ń‹ «ļÕő“…ķ√Ł”–ĻōŌĶĶń∂ęőų£¨ő“«∑ő“łł«◊Ķń°£ő“√Ľ”–ŌŽĶĹ£¨ 곍ÕÍŃňļů£¨ő“ĽŠ‘Ŕ“ĽīőĽōĶĹ√ļŅů°£Ņ…ń‹ 곍 «Ķŕ“ĽĽōŐŠ–—ő“£¨ő“√Ľ”–ĶĪĽō ¬, ĽĻľŐ–ÝĽ≠Ľ≠°£ őńļ££ļő“Ņīń„Ķń 곍 «∑«≥£ĺŖŌůĶń°£Ī»»Áń«łŲĻ—łĺÕŪ…ŌŐ…‘ŕī≤…Ō£¨ňż Ň»•’…∑ÚĶńŃťĽÍ‘ŕŅī◊Ňňż°£ĽĻ”–ňņ”ŕÕŖňĻĪ¨’®ĶńŅůĻ§“ŇŐŚ£¨ŌŮļž Ū°£ Ń÷Ųő£ļ”–»ňňĶ£¨ĹŲī”ő“Ķńĺ≠ņķņīŅī£¨“™ňĶ√Ľ”–…Ů£¨ňŻ√«∂ľ≤ĽŌŗ–Ň°£ő“Ľ≠Ľ≠£¨ő“Ňń…„ľÕ¬ľ∆¨£¨ő“…ķ√Ł÷–Ķń√Ņ“Ľ≤Ĺ£¨∂ľ «ń«—ý»√»ň≤ĽŅ…ňľ“ť°£°∂≥¬¬Į°∑’‚≤Ņ”į∆¨ÕÍ≥…Ńň£¨Ķęő“≤Ľ÷™ĶņŌ¬“Ľ≤Ņ£¨ő“÷Ľ÷™Ķņ“™ŇńłłĪ≤ń«Ňķ»ň°£ Ķľ …Ō£¨ń«Ňķ»ň‘ŕńń∂ýő“∂ľ≤Ľ÷™Ķņ£¨Ķęő“Ķń∆¨◊”ÕÍ≥…Ńň°£÷Ľ «Ķž۾≠Ķń ĪļÚ£¨ő“∑ĘŌ÷ő“ĶĪ ĪĻĻňľĶńń«łŲņ∂ŐžĺĶÕ∑∂ŗ”ŗŃň°£ő“ňĶ£¨…ķĽÓĶńľŠ”≤“—ĺ≠—ňłÓŃňňý”–Ķń „«ť£¨“—»›≤ĽŌ¬»őļő ę“‚ļÕ „«ť£¨ń«łŲĽ≠√ś «∂ŗ”ŗĶń°£≥ťĶŰ£¨ňŁ≤ĽĪĽ»›–Ū°£

őńļ££ļ‘ŕ’‚łŲĻż≥Ő÷–£¨”¶ł√ «ľ«“š“ĽĶ„“ĽĶőĶōŌÚń„≥®Ņ™į…? «“ĽłŲ‘ű—ýĶń»Ō ∂Ļż≥Őńō? Ń÷Ųő£ļń«łŲ ĪļÚÕ¶∆ī√ŁĶń£¨”–Ņ’ĺÕŇń°£ŇńĶń ĪļÚ «’‚—ýĶń£¨“ĽłŲłŲĶō’“’‚–©ŅůĻ§°£ń«łŲ ĪļÚĺÕ «∆ĺ÷Īĺű£¨√Ľ”–Ļż∂ŗĶńŌŽ∑®£¨‘łÕŻ“≤∑«≥£∆’Õ®°£ő“ĺűĶ√ő“«∑ő“į÷£¨ő“Ľ≥ńÓő“Ķńłł«◊£¨Ķęő““—ĺ≠√Ľ”–įž∑®Ňńő“į÷Ńň£¨÷Ľ”–Õ®ĻżĻ§”—ŐłŐłňŻ£¨»√ňŻ√«Ĺ≤łÝő“Őż°£ł’Ņ™ ľő“ĽĻ–īŇń…„‘żľ«£¨ļůņī,Ňń…„Ķŕ“ĽŐžő“◊įŃňľłŇŐīŇīÝ»•£¨īŇīÝ≤ĽĻĽĺÕłŌĹŰīÚĶÁĽį»•ń√°£°∂≥¬¬Į°∑◊‹Ļ≤≤ŇŇńŃň8ŇŐīŇīÝ°£’‚Ķŕ“ĽŐžŇńő““Őłł“ĽłŲ»ňĺÕŇńŃň10ŇŐ°£ňŻňĶĶńń«łŲĻ ¬ĺÕŌŮ’ż‘ŕ∑Ę…ķ£¨ŌŮłķŇń“Ľ—ý£¨Ō∑ĺÁ–‘ňś Ī‘ŕÕ∆ĹÝ£¨Ĺť…‹∂‘Ōů—Ĺ£¨Ĺ”◊Ň“Ľ–©¬“∆Ŗįň‘„Ķń ¬«ť°£◊Óļů∂ľ≤Ľ÷™Ķņ «’¶Ľō ¬£¨◊ÓļůľŰľ≠Ķń ĪļÚ‘Ŕ¬ż¬żňľŅľ»•į…°£ń„≤Ľń‹Õ££¨“≤≤Ľ÷™Ķņ’¶Ľō ¬£¨“≤≤Ľ÷™ĶņĽŠ∑Ę…ķ…∂£¨īŇīÝ≤ĽĻĽĺÕ¬Ú…Ō“ĽŌš¬ż¬żŇ™£¨“ĽĻ≤ŇńŃň72ŇŐ°£Ňń…„Ļż≥Őļ‹ĹŰ’Ň£¨ņŘĶ√≤Ľ––°£»Ľļů£¨ĹŰĹ”◊Ň…ŌőŚŐžįŗ£¨…ŌÕÍőŚŐžįŗĽōľ“ĺÕňĮĺű£¨Ķ»”ŕ «–›ŌĘ°£‘Ŕ∆ī÷‹ń©ń«ŃĹŐž£¨’“»ňŇń°£ő“ÕÍ»ę «√£»ĽĶń£¨ĺÕ «Ňń—ĹŇń°£ ‘ŕ’‚Ļż≥Ő÷–ő“ł–ĺűĶĹ£¨ő““‘ő™÷ģ«į◊‘ľļ–īĻż ę£¨“‘ő™ő“‘ŕŅů…Ō≥§īů£¨“‘ő™ő“∂‘ŅůĻ§ļ‹ŃňĹ‚°£ļůņī∑ĘŌ÷, ŇńĶĹĶńĪ»ŌŽŌŮĶńłī‘”°Ę∑ŠłĽŐę∂ŗŃň£¨łŲ»ňĶń ”“į∆š Ķ «∑«≥£–°Ķń°£Ňń÷ģ«į£¨ő“‘ű√īń‹ŌŽĶĹő“ĽŠŇńĶĹÕĮĻ‚ńō?ń«łŲ»ňő“‘≠Ō»∂ľ’“≤Ľ◊Ň£¨ľłļű‘ŕ∑Ň∆ķĶńĪŖ‘ĶĶń»ň£¨ő Ńň∂ŗ…Ŕ»ň—Ĺ£°◊Óļů£¨÷’”ŕŇŲĶĹňŻń«łŲ«ÝĶń«Ý≥§£¨ňŻő :°łń„’“ň≠?°Ļő“ňĶ:°łÕĮĻ‚£¨…Ōļ£ņīĶń°£°ĻňŻňĶ:°łń„łķő“⾛◊Ŗ°£°Ļ◊ŖĶĹ…Ĺ∂•…Ō£¨ĺÕļį:°łÕĮĻ‚£¨≥Ųņī°£°ĻňŻ «ŃžĶľ¬Ô, ń«ņŌÕ∑“ĽŐżĺÕŖňŖňŖňĶō◊Ŗ≥ŲņīŃň°£ňŻňĶ:°ł’‚∂ý”–»ň’“ń„°£°Ļő““≤ĺÕ»Á∑®Ňŕ÷∆ĶōļÕňŻňĶ:°łő“ŌŽŇńŅůĻ§°£°Ļ ňŻňĶ:°łő“ļÕňŻ√«≤Ľ “Ľ—ý°£°Ļő“ňĶ:°ł∑ī’ż «“ĽŅťņīĶń°£°Ļ ļůņī£¨ňŻ“ĽĹ≤£¨÷ĪĹ”ĺÕį—ő“łÝ’ūīŰŃň°£Īĺņī «ŌŽŇńŅůĻ§√«ĶńŅŗń—,◊Óļů ¬«ť»ī «’‚—ýĶńłī‘”°£ő“ł’Ņ™ ľĽĻ”Ő‘•£¨ňŻĶńĺ≠—ĻłýļÕŅŗń—√Ľ”–ĻōŌĶ°£ňŻ‘ŕ…Ōļ£ «łŲĽžĽž£¨łķĻķ√ŮĶ≥°Ę»’ĪĺĻŪ◊”°ĘĻ≤≤ķĶ≥īÚĹĽĶņ, ◊Ų“©…ķ“‚Ķ»Ķ»°£ ňŻ∑«≥£÷ų∂Į°Ę◊Í”™ľ”»ŽĶĹőųĪĪīůŅ™∑Ę£¨ĽžĶĹ’‚łŲ∂”őťņÔ£¨ŌŽŐ”Ī‹÷∆≤√£¨◊ÓļůĽĻ «ĪĽĻōĹÝľŗ”Ł£¨…ŌĶű◊‘…Īőīňž°£’‚łŲ»ňőÔÕÍ»ęļÕŅůĻ§Ķń√Ł‘ň≤Ľ“Ľ—ý°£ ő“ő™ ≤√īňĶ£¨ľÕ¬ľ∆¨Ķľ—›Ķń…Ū∑› «ĪįőĘĶń?ń„÷Ľń‹÷“ Ķ°Ęĺ°Ņ…ń‹÷“ ĶĶōĹę…ķĽÓ◊™ĽĮő™”įŌŮ£¨»őļő唳ŖŃŔŌ¬Ķń…ů ”ļÕőš∂Ō£¨∂ľĽŠ Ļń„Ķń”įŌŮŅ…“…°£ń„√Ľ”–»®ņŻ»•—ňłÓňŁ°£ń„ŇńĶĹŃňňŻ£¨ń«ĺÕ «»żņÔ∂īŅůĻ§…ķĽÓĶń“Ľ≤Ņ∑÷£¨ń„łýĪĺ√Ľ”–»®ņŻ»•—ňłÓĶŰ°£ŇńĶĹ ≤√ī°Ę”į∆¨ «‘ű—ý£¨łýĪĺ≤Ľ «ő“ňĶŃňň„Ķń£¨ «…ķĽÓňĶŃňň„°£ő“ŇńŌ¬ņī°Ęő“ľŰľ≠Ķń «…ķĽÓĶńŇ®ňű°£ő“÷Ľń‹÷“ Ķ”ŕŅīĶĹĶń…ķĽÓ£¨ĪĺņīĶń√ś√≤©§©§ ňŁĶń’śŌŗ°£ő“łýĪĺ√Ľ”–»®ņŻĹę’‚łŲ»ňī”ľÕ¬ľ∆¨÷–≥ťĶŰ£¨”–»ňŅ…“‘£¨Ķęő“≤Ľ––£¨’‚ «“Ľ÷÷◊‘ĺű°£ őńļ££ļĶęń„“≤ «ī”…ŪĪŖ◊‘ľļĶń ¬°Ęľ«“š°Ęłł«◊ĶĹÕ¨—ßŇń∆ū°£ń„◊ÓĹŁĶń”į∆¨ «°∂ÕŖňĻ°∑£¨“—ĺ≠…śľįĻęĻ≤ ¬ľĢ£¨ĽĻ»•őųį≤Ňń…„Ńň°£ Ń÷Ųő£ļ“≤≤Ľ «◊‘ĺűĶń°£Ķę◊Ų≥Ųņīļů£¨Īū»ňŅīĶĹ’‚—ýĶńĹŠĻŻ£¨≤Ň’‚—ýŌŽ°£ő™ļő“™Ň‹ĶĹőųį≤»•Ňń…„?“Úő™’‚łŲ ¬ľĢ «Ĺ®Ļķļů44ńÍņī◊ÓīůĶńÕŖňĻĪ¨’®°£Ō÷‘ŕŅůń—≤Ľ∂Ō£¨ĽĻ”–ň≠ľ«Ķ√ńō?ő“ «ĺ‹ĺÝ“ŇÕŁĶń°£ő™…∂◊ųľŻ÷§?“Úő™»ň√«Őę»›“◊“ŇÕŁŃň°£ Ňń°∂»żņÔ∂ī°∑£¨ő“ĶĹ…¬őųÕ≠ī®Õűľ“ļ”ŅůĶń ĪļÚ£¨ő“–° ĪļÚľ«“š»Áīň…ÓĶńŅů≥°£¨ĶęĶĪő“»•’“Ķń ĪļÚ»ī’“≤ĽĶĹŃň°£ń«√ī žŌ§ĶńĶō∑Ĺ£¨»ī‘ű√ī“≤’“≤Ľ ĶĹ°£ő“ő ÷‹őßĶń»ň“≤≤Ľ÷™Ķņ°£ļůņī£¨”ŲľŻ“ĽłŲņŌĻ§»ň£¨ő :°łÕűľ“ļ”Ņůĺģ‘ŕńń∂ý?°ĻňŻňĶ:°ł‘ŕńń∂ý?ĺÕ‘ŕ’‚ņÔ°£°ĻĹŠĻŻ“—ĺ≠ĪĽŐÓ¬ŮŃň, …Ō√ś «“ĽłŲňģńŗ≥ß°£ń„Ņī°∂»żņÔ∂ī°∑ ņÔ√ś£¨ń«√ī∂ŗĶō∑Ĺ”–ľŻ÷§, ĶęÕűľ“ļ”Ņů»ī≥ĻĶ◊ĪĽń®ĶŰŃň£¨÷‹őß «ňģńŗ≥ߣ¨ĺģ⼝ĪĽŐÓ¬ŮŃň,“ĽĶ„ļŘľ£“≤√Ľ”–ŃŰŌ¬°£ņķ ∑ĺÕ «’‚—ý£¨ő“ĶĪ ĪĺűĶ√»ÁĻŻ≤Ľľ«¬ľŌ¬ņī◊ųľŻ÷§£¨ĺÕŌŻ ßŃň£¨√Ľ”–Ńň°£ ĶĹŇń°∂ÕŖňĻ°∑Ķń ĪļÚ”÷ «’‚—ý£¨ő“Ņ™ ľ‘ŕ≥¬ľ“…ĹŅů≤…∑√£¨Ĺ”◊Ň «Õ≠ī® –£¨‘ŔĺÕĶĹőųį≤Ľū≥Ķ’ĺ£¨ń«ņÔ”–ņī◊‘»ęĻķłųĶōĶń»ň°£”–“ĽłŲ¬ŰĪ®÷ĹĶńňĶ:°ł’ŻŐž «’‚∂ýĪ¨’®°Ęń«∂ýĪ¨’®Ķń£¨ő“∂ľ≤Ľľ«Ķ√ «ńńīőĪ¨’®Ńň°£°Ļ ”–“Ľīőő“‘ŕňő◊Į∑Ň”≥°∂ÕŖňĻ°∑£¨Õ¨“Ľ ĪŅŐ£¨Õ≠ī®Ķń“ĽłŲŅů”÷∑Ę…ķĪ¨’®Ńň£¨ ≤ųŠĹ–°łĻ≤ Ī–‘°Ļ—Ĺ£Ņ’‚ĺÕĹ–Ļ≤ Ī–‘°£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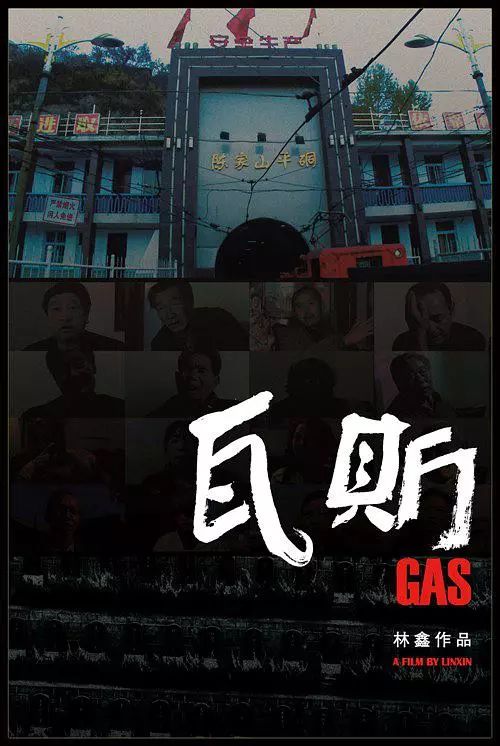
Ňń∆¨ «∂‘…ķ√Ł≤Ľ∂ŌÕÍ…∆ĶńĻż≥Ő
őńļ££ļń„∂‘Ō÷Ĺ◊∂ő÷–Ļķ∂ņŃĘľÕ¬ľ∆¨ĶńŅī∑®?Ń÷Ųő£ļňýőĹ∂ņŃĘ£¨ő“ĺűĶ√”¶ł√ «īī◊ų°Ę—°∆¨°Ę∆ņ¬Řłų∑Ĺ√ś∂ľ «∂ņŃĘĶń£¨ÕÍ»ę «ń„∂ņŃĘňľŅľ≥ŲņīĶń∂ęőų£¨≤Ľ≥ľ∑Ģ”ŕ»őļő»ň£¨≤Ľ «ĪĽ—ňłÓĶń°£’‚łŲ∂ņŃĘ“≤ «◊‘–Ň–ńĶń≥…≥§°£Ō÷‘ŕő“Ī»‘≠ņī«ŅīůĶ√∂ŗŃň£¨‘≠ņīļ‹–ť»ű°£»ÁĻŻ”į∆¨ĪĽ—°ĹÝń≥łŲĶÁ”įĹŕ£¨ĺÕ”¶ł√ň„ļ√◊ų∆∑į…£°°∂≥¬¬Į°∑»ÁĻŻ√Ľ”–—°…Ō£¨Ņ…ń‹ĺÕĪĽ»Ōő™≤Ľļ√£¨ĶĪ Īő“ «√Ľ”–ń«łŲ◊‘–Ň–ń°£ Ō÷‘ŕ,°∂≥¬¬Į°∑ń‹ĻĽ≤őľ”Ļķľ ĶÁ”įĹŕ£¨Ķę°∂»żņÔ∂ī°∑»ī≤őľ”≤ĽŃň°£ Ķęő““Ľ—ý»Ōő™°∂»żņÔ∂ī°∑Ī»°∂≥¬¬Į°∑ļ√ļ‹∂ŗ£¨ő““ĽĶ„∂ľ≤ĽĽ≥“…°£÷Ľ“™¬ż¬ż◊ŲĺÕĽŠ∂‘◊‘ľļ◊ų∆∑Ķń∑›ŃŅ≤ķ…ķ◊‘–Ň°£◊Óļůń„≤ĽĽŠ‘ŕļű”–őřĻŘ÷ŕ°ĘňŻ√« «∑ŮÕň≥°£¨’‚ «◊‘ő“Ķń≥…≥§°£’‚“≤ «ő“√«Īō–Ž⾯√ś∂‘Ķńő Ő‚°£’‚“ĽĻōīůľ“ŅÁĻż»•Ńň£¨≤Ľ «“ĽłŲ»ň∂Ý «“ĽŇķ»ň£¨ «“ĽłŲ Īīķ◊Ŗ…ŌŃň“ĽłŲłŖ∂»°£…Į⼠ ŅĪ»—« ĪīķĺÝ∂‘≤Ľ «Ļ¬ŃĘĶń£¨ń« «“ĽŇķ»ň“Ľ∆ū◊Ŗ…Ō»•Ķń£¨∂ÝňŻ «∂•∑Ś°£ĶĪŌ¬÷–ĻķľÕ¬ľ∆¨ĺŖ”–Ńňń«—ýĶń«ų ∆°£ŐžńŌļ£ĪĪĶńľÕ¬ľ∆¨◊ų’Ŗ£¨»ÁÕ¨“į≤›“Ľį„∆ī√Ł’ű‘ķ◊Ňī” Į∑ž÷–ī©≥Ų£¨łų…ę»ňĶ»°Ę…Ū∑÷łī‘”°ĘńÍŃšŅÁ‘Ĺľłīķ»ň£¨»ę∂ľ‘ŕҨѶ°£∂Ý«“≤Ľ÷™ĶņĽĻĽŠ”–ň≠ī”ńńņÔĪŇ≥Ųņī°£‘ŕ’‚łŲ»ļŐŚĪ¨∑Ę÷–£¨’ŻłŲ––“ĶĶńňģ◊ľ∂ľŐŠłŖŃň°£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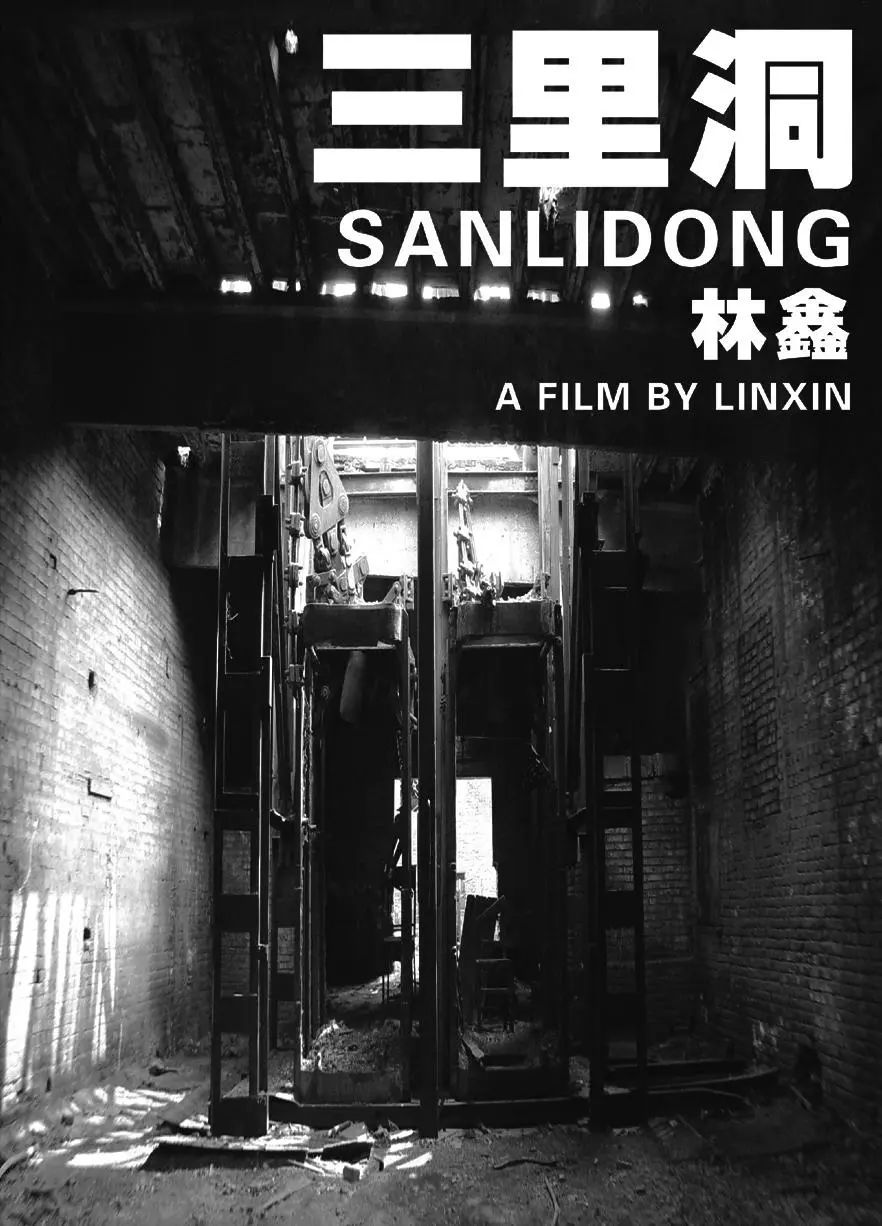
őńļ££ļń„Ō÷‘ŕĶńī¶ĺ≥? Ń÷Ųő£ļ°į≥¬Ļ‚≥Ō ¬ľĢ°Īő““≤ļ‹Ļō◊Ę°£ļůņī≥¬Ļ‚≥ŌŐ”◊ŖŃň£¨ŃűŌĢ≤®ĪĽĻōŃň£¨”ŗĹ‹“≤ŃųÕŲŃň°£Ķęń„∑ĘŌ÷÷–Ļķ’‚√īīů£¨–Ū÷ĺ”ņ”÷≥ŲņīŃň°£÷–Ļķ’‚łŲ√Ů◊Śń„őř∑®ŌŻ√ū, ”–ń«√ī∂ŗĶń»ň«į∆ÕļůľŐ£¨ňŻ√« «––∂Į’Ŗ, Õ∆∂Į÷–ĻķŌÚ«į––°£Ķęő“≤Ľ «ń«—ýĶń»ň£¨ő“√«”–ő“√«Ķń’ůĶō£¨ő“√«Õ¨—ýŌ£ÕŻ◊‘ľļĶńĻķľ“ļ√°£ĶĪ»Ľ£¨Ļķľ“≤Ľ «’Ģłģ°£ő“√«…ķĽÓ‘ŕ’‚∆¨ÕŃĶō…Ō£¨ő“”ņ‘∂ł––Ľ’‚∆¨ÕŃĶō£¨ő“≤ĽĽŠņŽŅ™’‚∆¨ÕŃĶō°£Ķęő“√«”–∑÷Ļ§£¨ő“‘ŕő“ń‹ĻĽī” ¬ĶńŃž”Ú£¨ő“ń‹ĻĽ◊ŲĶń£¨ő“ļŃ≤ĽÕ◊–≠£¨“Ľ≤Ĺ≤ĹĶō»•◊Ų°£ő“ «»Ū»űĶń£¨ĶĪ»Ľ”– ĪļÚ“≤ļ¶Ň¬°ĘŅ÷ĺŚ£¨ő“√« «»ň°£ő“ī”ņī≤ĽŌÚÕýŃűļķņľ£¨ő“»Ōő™ń«–©”Ę–ŘņŽő“√«Őę‘∂£¨’ś’ż»√ő“ł–∂ĮĶń «őų√…ń»‧řĪ“ņ°£ő“»Ōő™ňż «őįīůĶńĽý∂ĹÕĹ°£◊Óļůňż’ű‘ķń«√īĺ√, “≤√Ľ”– ‹Ōī°£Ķę“Úő™’‚Ķ„£¨ń„ĺÕ≤Ľ≥–»Ōňż «Ľý∂ĹÕŬū?ňż «≤Ľ «Ľý∂ĹÕĹ,≤Ľ÷ō“™°£ ‘ŕ°∂ļŕįĶ÷–ĶńőŤ’Ŗ°∑’‚≤Ņ∆¨ņÔ£¨◊Óļůňż(∆¨÷–Ňģ÷ųĹ«…Į¬Í)÷™ĶņĺĮ≤ž(ňżĶń∑Ņ∂ę)įÔ÷ķĻżňż,∂Ý≤Ľ‘łĹ“¬∂ňŻĶń◊Ô––£¨į—Īū»ň÷√”ŕ≤Ľ“ŚĶńĶō≤Ĺ°£ňš»ĽňŻÕĶŃňňżő™÷ő∂ý◊”—Řľ≤Ķń«ģ,≤Ę‘ŕňŻ”’ĶľŌ¬Ņ™«Ļ…ĪŃňňŻ°£ňż—°‘Ů≥– ‹’‚—ýĶń√Ł‘ň°£ĶĪňż“„»Ľ◊ŖŌÚ–Ő≥° Ī£¨ňż—°‘ŮĹ –Ő, Ķę «ňżňĶ:°łő™ļőő“ĶńÕ»‘ŕ∑Ę∂∂?°ĻŅīĶĹń«“Ľ∂ő£¨ő“ņŠŃų¬ķ√ś£¨‘ŕ»Ū»ű÷–ń„Īō–Ž◊ŖŌ¬»•£¨ń„–ńĽ≥Ņ÷ĺŚ£¨Ķęń„√Ľ”–Õň¬∑, “Úő™ń„—°‘ŮŃň’‚—ýĶń“ĽŐű¬∑°£ ’Ģ÷őľ“”–’Ģ÷őľ“ĶńĻ§◊ų£¨––∂Į’Ŗ»•◊Ų––∂Į’Ŗ°£’ż»ÁÕű–°¬≥ňĶĶń£¨’‚ «ļŕįĶ÷–ĶńĻ‚ŃŃ°£’‚÷÷Ļ‚ŃŃ£¨ő“√«√ŅłŲ»ň∂ľ“ĽĶ„“ĽĶ„Ķō‘ŕ∑Ę≥Ų£¨◊Óļů£¨Őž√ųĪōĹęĶĹņī°£ő“‘ŕŇń…„°∂īęĶņ»ň°∑Ķń ĪļÚ£¨ŃžĶľ’“ő“ŐłĽį£¨ő“ňĶ:°ł∑®¬……ŌĻś∂®÷–Ļķ”–◊ŕĹŐ–Ň—ŲĶń◊‘”…°£°ĻňŻňĶ:°ł÷–Ļķńń”–∑®¬…?÷–ĻķĺÕ√Ľ”–∑®¬…!°Ļő“ňĶ:°ł «Ķń£¨Ķę’‚Ľįń„÷Ľń‹‘ŕ◊ņ◊”Ķ◊Ō¬ňĶ£¨’‚ «√Ľ”–įž∑®ń√ĶĹ◊ņ√śĶń°£°Ļő“ňĶ:°łő“ľŠ–Ň÷–ĻķĽŠ“ĽĶ„“ĽĶ„ĹÝ≤Ĺ£¨ń„√«Ō÷‘ŕŅ…“‘Őį‘ŖÕų∑®°Ęļķ◊ų∑«ő™£¨Ķę÷–Ļķ◊‹”–“ĽŐžĽŠ◊Ŗ…Ō∑®÷∆ĻžĶņ£¨◊ŖŌÚ√Ů÷ų£¨ĽŠĹÝ≤ĹĶń°£°Ļ ňý“‘£¨ő“≤Ľń√Īū»ňĶń“Ľ∑÷«ģ£¨»ę≤Ņ◊‘ľļÕ∂»Ž°£“Úő™ő“÷™Ķņń√ŃňĪū»ňĶń«ģ£¨»√ń„łń£¨ń„łń≤Ľłń?ő“∂‘◊ų∆∑”–ÕÍ»ęĶń’∆Ņō»®£¨ő“∂‘Ńľ–ń°ĘŃľ÷™£¨”√ő“ĶńļůįŽ⽣…ķ»•łļ‘ū£¨ ≤√ī∂ęőųő“∂ľ≤ĽŅľ¬«°£ĶĪń„“„»ĽĺŲ»ĽĹęļůįŽ…ķ»ę≤ŅÕ∂»ŽĹÝ»•Ķń ĪļÚ£¨ ≤√ī∂ľ≤Ľ‘ŕļűŃň°£ń„≤ĽŇ¬ňņ£¨ĽĻҬĽÓ?Ķę «£¨ő“≤Ę≤Ľ“™ĶĪ”Ę–Ř∂ÝňņĶŰ°£’‚÷÷÷ōĹ®ĶńĻ§◊ų, ő“Īō–Ž»•◊Ų£¨◊ŖŌ¬»•£¨’‚ «ő““™◊ŲĶń°£ľī Ļī”◊Ó◊‘ňĹ◊‘ņŻĶńĹ«∂», ĹŲĹŲő™Ńňő“łŲ»ň,ő“»‘ «◊ÓīůĶń ‹“ś’Ŗ£¨’‚ «∂‘…ķ√Ł≤Ľ∂ŌÕÍ…∆ĶńĻż≥Ő°£ĶĪ»Ľ£¨ňŁ∂‘…ÁĽŠ“≤ «”–“śĶń£¨’‚÷÷Õ∆∂Į≤Ľ–Ť“™»őļő÷§√ų°£ |